这是我父亲的尺子。
记忆里,父亲的手总是很大,指节粗壮,掌心布满粗糙的老茧。那双手能抡起沉重的铁锤,也能把一颗小小的螺丝拧得恰到好处。可当他拿起这把尺子,为我检查作业时,动作却出奇地轻柔、仔细。他会把尺子端端正正地压在本子的横线上,眯起那双因常年劳作而有些浑浊的眼睛,顺着刻度一寸一寸地看过去。
“这里,歪了。”他的声音低沉,带着不容置疑的肯定。
我那时正上小学,最烦的就是他检查作业。别的同学家长大多只看对错,只有他,对我的字迹是否工整、线条是否笔直,有着近乎偏执的要求。我常常不耐烦,嘟着嘴,心里埋怨他小题大做。不就是几个字吗,写对了不就行了?他不多解释,只是沉默地把尺子递过来,那意思再明白不过:重写。
橘黄色的灯光下,我憋着一肚子委屈,重新趴回桌子上。他就坐在我旁边,也不做别的事,只是静静地陪着。房间里只有铅笔划过纸张的“沙沙”声,和他偶尔因为疲惫而发出的轻微叹息。我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、混合着机油和汗水的气味,那是我童年最熟悉的味道。有时,我用余光偷偷看他,他靠在椅背上,眼神有些放空,不知在想些什么。是在想今天车间里没做完的活儿,还是在想明天一家人的开销?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,他那紧锁的眉头里,藏着生活的重量。
那把尺子,就成了我们父子之间一种沉默的交流工具。它量出的,不只是我笔下线条的曲直,更像是一种他试图传递给我的、关于“规矩”的东西。他自己没读过多少书,一辈子和钢铁、机器打交道,他相信,这个世界是有标尺的,做事要横平竖直,做人要规规矩矩。他没法用华丽的语言告诉我这些道理,只能用这把最朴素的尺子,在我的人生白纸上,画出最初的那条基准线。
后来,我上了中学,功课越来越难,他已经辅导不了了。那把尺子也就渐渐退出了我的书桌。它被他收了起来,不知放到了哪里。我们之间的交流,也像那把被收起的尺子一样,变得越来越少。我进入了所谓的叛逆期,觉得他的那一套“规矩”早就过时了。我们开始因为一些小事争吵,为我的发型、为我晚归的时间、为我那些在他看来不切实际的想法。我觉得他不懂我,而他,只是用更深的沉默来应对我的激烈。
那时,我只想快点长大,快点逃离那个被他的“尺子”框住的家。
再后来,我真的离开了家,去外地读大学,然后工作、成家。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和父亲通话,也总是那几句“吃了没”、“钱够不够花”、“注意身体”。我们之间,仿佛隔了一层无形的、却无法捅破的窗户纸。我知道他爱我,他也知道我爱他,但我们都不知该如何表达。
直到前年春天,母亲打电话来,说父亲在收拾家里的旧物。我回去帮忙,在书房那个老旧的抽屉里,我又看到了它——那把塑料尺子。它安静地躺在那里,仿佛这二十多年的时光从未流逝。我拿起它,那一刻,所有关于橘色灯光、关于沙沙写字声、关于他身上那股机油味道的记忆,汹涌地扑面而来。
母亲在一旁轻声说:“你爸一直收着呢,说这是你小时候用的东西,留个念想。”
我握着那把尺子,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我忽然全都明白了。当年那个沉默寡言、用尺子逼着我把字写工整的父亲,他倾其所有,想给我的,不过是一种能力——一种能让人生在复杂世界里保持笔直、不至于走歪的能力。他把他所能理解的、最宝贵的“正直”与“认真”,都凝注在这把小小的尺子里了。
如今,我也成了别人的父亲。我的书桌抽屉里,有电脑,有平板,有各种先进的办公用具。可我还是把父亲这把旧尺子带了回来,放在了最显眼的地方。当我为了一个项目焦头烂额时,当我因为周遭的浮躁而感到迷茫时,我会拉开抽屉,看看它。
它不再是一把衡量物理长度的工具了。它是我人生的坐标轴。那一格一格的刻度,量过的是我歪歪扭扭的童年,量过的是父亲沉默而深厚的期望,也量着我从一个叛逆少年,到终于理解何为责任的这整个漫长过程。
父亲老了,背有些驼了,那双手也不再那么有力。我们坐在一起,话依然不多,但不再有从前的紧张与隔阂。有时,我会跟他讲讲我工作上的事,他听着,偶尔点点头,说一句:“嗯,心里有杆秤就行。”
我心里那杆秤的定盘星,就是这把已经泛黄、磨损的塑料尺子。它很轻,轻得几乎没有重量;它又很重,重得承载了一个父亲全部的爱与期盼。它就那么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,像一个沉默的守护者,提醒着我,无论走到哪里,走了多远,都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个起点,不要忘记那条用爱画下的、笔直的线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八亿典藏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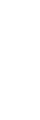 八亿典藏文章
八亿典藏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34)
1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22)
2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115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2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0)
5因为小事吵架冷战,他先发来 “想你了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