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活儿,是从备料开始的。沙子得用河沙,细腻,没那么多杂七杂八的土疙瘩。水泥呢,标号要对,不能图便宜。和灰的时候,水要一点点地加,手里的铁锹一下一下地翻着,搅着,直到那灰成了均匀的膏状,不稀不稠,黏糊糊地扒在锹上,又不至于滴落下来。这功夫,全在手上,在眼里,没个几年,摸不准那个分寸。灰和好了,就算开了个头。
上墙是力气活,也是手艺活。左手托着灰板,右手握着抹子,一剜,一甩,那团湿漉漉的灰泥便“啪”地一声,服服帖帖地粘在了墙上。接着,抹子就得跟上,横着、竖着、斜着,一遍遍地刮,一遍遍地抹。手腕子要活,力道要匀。劲儿大了,把底子带起来了,这墙将来准裂;劲儿小了,灰和墙粘不实在,空鼓了,那也是败笔。得让那灰吃进墙里,像是从墙里头自己长出来的一层新皮肤。抹的时候,眼里得有线,心里得有谱,高一点,低一点,都得在这来回的抹刮里找平喽。这当口,人是不能分心的,世界好像就剩下了眼前这堵墙,手里的这把抹子,还有那“沙沙”的,灰泥被抹平的声音。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淌,有时候流进眼里,涩得生疼,也顾不上擦,只能使劲眨巴几下。衣服后背上,总是结着一层白花花的汗碱。
等到最后一遍收光完成,手里的抹子离开墙面,人会不自觉地往后退两步。这时候,腰背的酸、胳膊的沉,才一股脑地涌上来。可你还顾不上这些,你得先看。看这新抹的墙面,是不是光溜得像大姑娘的脸蛋,平得像一面镜子。光线从窗户斜打进来,照在上头,泛着一种湿润的、沉静的青灰色光泽。到了这一步,我这泥水匠的活儿,就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。剩下的,就是交给时间,等着它自己慢慢地、慢慢地干透。
这等待的工夫,最是磨人,也最有意思。
刚抹好的墙,是不能急的。你凑近了,能闻到一股子土腥气混着水汽的味道,生涩,但是清新。墙是不能吹穿堂风的,那样干得太快,外头干了,里头还潮着,非得裂开不可;也不能让日头直晒,一晒,也保准完蛋。就得那么阴着,让它自个儿慢慢地、由内而外地吐纳。我常常就搬个小马扎,坐在离墙不远不近的地方,点上一支烟,静静地瞧着它。
头一两天,那墙的颜色变得最快。从刚完活儿时那种饱含水分的深青灰,一点点地淡下去,变成浅灰,像黎明前天空的颜色。墙面上的湿气,一丝一丝地收着,你仿佛能听见它收缩时那种极其微弱的、窸窸窣窣的声音。那是一种内在的力量,看不见,但你能感觉到。墙,好像在呼吸。
有时候,看着看着,会想起这墙背后的人家。这一抹,也许就圈定了一个小伙子的新房,将来这里会贴上喜字,充满欢声笑语;也许是为一个操劳了半辈子的老人家,修补了漏雨的旧屋,能让他睡几个安稳觉;又或者,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厨房,女主人会在这里为全家准备一日三餐,油烟会渐渐熏黄这此刻还崭新的墙面。我这手里的灰泥,抹上去的,不只是一堵墙,更像是一个壳,一个背景,往后日子里头的酸甜苦辣,都得在这背景前头,一幕一幕地上演。这么一想,手底下的活儿,就更不敢有丝毫马虎了。我这粗糙的手,抹出的每一平方面,都连着别人家的日子呢。
等到三五天过去,墙面的灰色变得更浅,更稳,像秋日里晒干了的瓦片。用手背轻轻地、试探着贴上去,那股子沁人的凉气已经没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吞的、干爽的触感。凑近了闻,土腥气也淡得几乎没有了,只剩下一种干净的、类似石头一样的味道。这时候,心就放下了一大半。知道这墙,算是稳当了。
最后,用指关节叩一叩墙面,发出“咚咚”的、结实的响声,清脆,不闷。这就成了!这面墙,从一堆散沙、一包水泥,经过我的手,和水调和,与墙相融,再在时光里静静地孕育、变化,终于有了自己的筋骨,能立得住,能经风雨了。它不再是我手下的一个活儿,它成了它自己,成了这房子的一部分。
我站起身,收拾好灰板、抹子,把它们擦得干干净净。回头再看看那面墙,它静静地立在那里,不言不语,却好像什么都说了。然后我推开门,走出去,把这一室的安静与圆满,留给它未来的主人。外头的阳光有些晃眼,我眯缝着眼,扛起工具,又走向下一个工地。生活,大概就是这样,一面墙一面墙地抹过去,在等待与劳作之间,日子也就这么实实在在地过下来了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八亿典藏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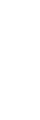 八亿典藏文章
八亿典藏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34)
1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22)
2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115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2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0)
5因为小事吵架冷战,他先发来 “想你了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