它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床头柜上,蒙了一层薄薄的灰。表盘是深邃的蓝色,像冻住的湖面,两根指针像两根冻僵的黑色枝桠,交叠着,固执地指向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时间。我每天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它,睡前最后一眼看到的也是它。我没有勇气去给它上弦,也没有勇气去调校时间,就让它那么停着吧,好像它停着,那个冬天就还没有完全过去,他就还没有真正走远。
他是我的父亲。
去年冬天,来得特别早,也特别冷。十一月的风就已经像小刀子一样,刮在脸上生疼。父亲的咳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加重的。他以前也咳嗽,老烟枪了,我们都习惯了。可那次不一样,那咳嗽声是闷的,是从很深很深的胸腔里发出来的,听着就让人心头发沉。我和母亲劝他去医院,他总是摆摆手,说老毛病了,天暖和了就好。他那块手表,那时候还走得好好的,每天清晨五点,雷打不动地把他叫醒。
那块表,跟了他十几年了,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工资给他买的。不是什么名贵的牌子,但他喜欢得不得了,从那以后就再没摘下来过。表带已经磨得露出了底下黄铜的原色,表壳上也有了几道细密的划痕。他说,这表准,耐用,像我。
后来,他终究是拗不过我们,去了医院。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天,我记得特别清楚。天阴沉沉的,像是要下雪,却始终憋着,让人透不过气。我从医生办公室出来,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诊断书,却觉得有千斤重。我走到走廊尽头,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,站了很久,很久。回到病房,父亲正靠在床头,望着窗外。他听见我进来,转过头,脸上很平静,甚至带着一点淡淡的笑意,问:“结果不好,是吧?”
我张了张嘴,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了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叹了口气,不是为他自已,那叹息里,全是替我、替母亲感到的难过和担忧。他伸出手,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,说:“没事,别怕。”
就是从那天起,我开始格外注意他手腕上的那块表。它还在滴滴答答地走着,记录着父亲所剩无几的时间。那声音,在我听来,不再是时间的韵律,而是生命流逝的倒计时,一声一声,敲在我的心上。
他住院的那段日子,是我成年以后,和他相处最密集的一段时光。我们的话反而不多,很多时候,就是静静地坐着。我给他削苹果,他慢慢地吃;我给他读报纸,他闭着眼睛听。有时候,他会突然说起我小时候的事,说我很小的时候,如何摇摇晃晃地扑向他;说我青春期时,如何为了一点小事跟他大吵一架;说我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,他如何在厨房紧张得手忙脚乱……他说这些的时候,眼神是悠远的,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柔和的光。那块表,就安静地贴在他消瘦的手腕上,秒针一圈一圈,无声地卷走那些泛黄的旧时光。
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。原本宽厚的手掌,变得干瘦,青筋毕露。只有那块表,还牢牢地戴在手腕上,似乎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。有一次,他睡熟了,我坐在床边,看着他凹陷的脸颊,听着他粗重的呼吸,心里疼得像针扎一样。我的目光落在那块表上,它还在忠实地工作着,分针刚刚跳过一格。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念头:如果我把表针往回拨,时间是不是就能倒流?父亲的病是不是就能好起来?
我当然没有那么做。我只是伸出手,极其小心地、轻轻地摸了摸那冰凉的表蒙子。那一刻,我多么希望我的手指能带有某种魔力啊。
他走的那天,是个难得的晴天。冬日的阳光,苍白无力,透过病房的窗户照进来,在地板上投下模糊的光斑。他是在凌晨安静地离开的,像睡着了一样。母亲伏在床边,压抑的哭声像受伤的动物。我呆呆地站着,大脑一片空白。我的视线,最终落在了他被安置在身体两侧的手上——左手的手腕是空的。
护士小声告诉我,她们整理遗容时,把手表摘下来,放在床头柜上了。
我走过去,拿起那块表。它还带着一点父亲身体的余温。表盘上的秒针,颤巍巍地,又努力向前跳动了几格,然后,就彻底停住了。它就停在了那个时刻,那个父亲离开我们的,去年冬天的,凌晨五点二十一分。
我把表带回了家,放在了它现在的位置——我的床头柜上。
没有了滴滴答答的声音,房间里有种奇怪的寂静。起初我很不习惯,夜里常常会醒来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后来我才明白,少的不是声音,是那个为我制造了这背景音几十年的人。
时间,并不会因为一块表的停摆而驻足。窗外的树绿了又黄,黄了又绿。我的生活也在继续,工作,吃饭,睡觉,偶尔和朋友小聚,表面上,一切似乎都已恢复了常态。只有我知道,心底的某一个角落,已经跟着那块表,一起停在了去年冬天。
有时候,夜深人静,我会拿起那块表,贴在耳边。里面是死一样的沉寂。可奇怪的是,我仿佛又能透过这沉寂,听到很多东西——听到他清晨在厨房为我准备早餐的叮当声,听到他看我取得成绩时爽朗的笑声,听到他晚年那压抑的、让人心疼的咳嗽声,听到他在病床上,用虚弱的声音对我说:“没事,别怕……”
这块停摆的表,成了一个永恒的坐标。它标记的不是一个冰冷的时间点,而是我人生中一个巨大而温暖的存在消失的瞬间。它提醒我,我曾经拥有过多么厚重的爱,也提醒我,我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它。
它停了,于是,关于他的许多记忆,反而在我心里愈发清晰地流动起来。它像一扇被冻结在时间里的门,我打不开,也关不上,只能隔着这扇冰冷的玻璃,久久地凝望那个已经远去的冬天,和冬天里的那个人。
或许,我永远都不会去动它了。就让它停在那里吧。停在去年冬天,停在有他的时光里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八亿典藏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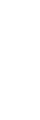 八亿典藏文章
八亿典藏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34)
1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22)
2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115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2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0)
5因为小事吵架冷战,他先发来 “想你了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