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记得特别清楚,是那种典型的、北方四月里的好天气。冬天那股子死缠烂打的寒气终于彻底松了手,阳光是金晃晃的,暖烘烘的,晒在皮肤上,不烫,只是一种妥帖的温暖,像刚喝下一口温润的粥。风呢,是主角,是那种被大家伙儿叫做“春日微风”的。它软软地、懒懒地吹过来,带着点儿刚翻过的泥土的腥气,混着远处不知名小花的淡香,还有新生树叶那种嫩得几乎要滴出水来的青涩味儿。它拂过脸颊的时候,不像冬天的风那样像小刀子,也不像夏天的风那样带着黏腻的汗意,它就是柔柔的,暖暖的,像最上等的丝绸轻轻滑过,又像谁在你耳边呵着气,低声说着安慰的话。
路上的行人,都仿佛被这风给浸透了。裹了一冬的厚重衣裳终于可以卸下了,人们穿着轻薄的春衫,脸上的表情也都是舒展的。我看见一个年轻的母亲,推着婴儿车,弯下腰,用手指着树梢上新冒的绿芽,轻声细语地对她咿呀学语的孩子说着什么。孩子咯咯地笑,小手在空中乱抓,好像想把那风、那阳光都攥在手心里。路边长椅上,一对老夫妇并肩坐着,老爷子闭着眼,仰着脸,任由阳光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流淌,老太太则安静地织着毛线,偶尔侧过头看他一眼,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那风,就环绕着他们,把老太太手里毛线的绒絮,吹得轻轻飘舞。
整个世界,包括我,都沉浸在这种被春天温柔包裹的幸福里。我的心也是轻快的,脚步也带着弹性,觉得生活里的一切烦恼,似乎都可以被这和煦的風吹散、化解。
可是,这风,这暖,偏偏没有吹到他身旁。
他住在城东那头的那家医院里。我是在去看他的路上,感受着这无边春意的。越靠近医院,我的心就越往下沉一点。推开那扇沉重的住院部的玻璃门,仿佛一步就跨入了另一个世界。门外是鲜活、流动的春天,门里是凝滞的、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、恒定的苍白。那味道,尖锐而冰冷,瞬间就刺破了春风在我身上留下的所有暖意和芬芳。
走廊又长又静,只有护士推着药车轮子发出的、规律而单调的辘辘声。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照进来,在地上拉出长长的、斜斜的光斑,能看见光柱里无数细小的尘埃在翻滚,但那光本身,却是冷的,没有了外面的那种金黄的暖色调。
我推开他的病房门。他躺在靠窗的那张床上,睡着了。被子盖到他胸口,显得他越发瘦削。床头柜上,放着吃了一半的、看上去就没什么滋味的病号饭,还有几只横七竖八的药瓶。窗户关得死死的,只留了一条小小的缝隙,用来换气。我走到窗边,透过那厚厚的玻璃向外看。楼下的小花园里,几株晚樱开得正热闹,粉粉白白的一树,同样有微风拂过,吹得那些花瓣簌簌地往下落,像一场绮丽的梦。
可这风,这暖,被这层冰冷的玻璃,严严实实地挡住了。它们属于外面那个自由的世界,却到不了他这里。
我坐回他床边的椅子上,静静地看着他。他的呼吸很轻,眉头即使在睡梦中,也微微地蹙着,像是在跟身体里某种看不见的痛苦较劲。他的脸色是那种久不见阳光的、带着点蜡黄的苍白。我忽然想起,就在去年这个时候,也是这样的春日,我们还在郊外爬山。他走在前面,回头冲我笑,额头上是细密的汗珠,阳光下,他的牙齿显得特别白。那时的风,吹动他微卷的头发,吹动他敞开的衣领,他张开手臂,几乎是拥抱着那阵风,大声对我说:“你看,活着多好!”
可现在,这该死的、温柔的、被所有人赞美着的春风,就在离他几米之外的地方自由地徜徉,却不肯,也不能,稍稍眷顾他一下。它吹绿了远山,吹皱了河水,吹开了百花,吹笑了孩童,却唯独绕开了这间小小的、安静的病房。它那样公平地赐福给万物,此刻在我眼里,却成了一种最残忍的偏私。
我甚至产生了一种荒谬的冲动,想过去把那扇窗彻底推开,让那风涌进来,灌满这屋子,吹到他的脸上,他的手上,或许就能把他眉间那个结吹开,把他脸上的苍白吹散,让他能像去年那样,再舒坦地叹一口气。
但我不能。他怕冷,一点风都不能受。
我就这么坐着,感觉自己被活生生地劈成了两半。一半的身体,还清晰地记得来时路上那春风的柔软触感,记得阳光照在脖颈上的微痒;另一半,却沉浸在这病房的清冷与寂静里,被一种无力的心痛紧紧地攥住。
他忽然动了一下,醒了。看见我,他努力地扯出一个笑容,那笑容虚弱得让我鼻子一酸。
“外面……天气很好吧?”他声音有些沙哑,轻声问。
我张了张嘴,那句“是啊,风很暖,很舒服”在喉咙里滚了几滚,终究没能说出来。我怎么能用我的感受,去对比他的处境呢?那太残酷了。
我最终只是点了点头,伸手替他掖了掖被角,说:“嗯,花都开了。”
他又笑了笑,重新闭上眼睛,像是连说这么一句话,都耗尽了力气。
那一刻,我无比真切地感受到,幸福与苦难之间,有时只隔着一扇窗,一层玻璃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不是天涯海角,而是春日温煦的微风就在窗外喧闹,却吹不到我所爱的人的身旁。
我依旧坐在那里,握着他放在被子外面、有些冰凉的手。窗外的世界,春光正浓,而那阵我来时一路陪伴我的、暖洋洋的微风,仿佛还在不知疲倦地吹着,吹过街道,吹过树梢,吹过所有能吹到的地方。只是我这里,我这颗心,再也感觉不到它的暖意了。它变成了一种背景,一种与我,与他,都无关的、遥远的喧哗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八亿典藏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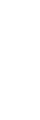 八亿典藏文章
八亿典藏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34)
1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22)
2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115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2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0)
5因为小事吵架冷战,他先发来 “想你了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