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住在山坳里,出门就是山,抬头还是山。记得七岁那年,我爬上村里最高的老槐树,站在树杈上踮起脚——山的那边还是山,层层叠叠,像永远掀不开的幕布。那天晚上,我在日记本上歪歪扭扭地写:我想看看山外面的世界。写完自己都笑了,这怎么可能呢?
父亲是石匠,他的手像山岩一样粗糙。他说咱们家三代人都在山里,山养活了咱们,咱们也离不开山。他叮叮当当地凿着石头,石屑飞舞中,他的话像刻进我心里:“人啊,要知道什么可能,什么不可能。”
可我心里总有个声音在问:真的不可能吗?
第一次觉得“不可能”开始松动,是十三岁那年。乡里来了支施工队,说要打隧道。他们穿着橙色工装,开着轰隆隆的机器。村里老人都摇头:“祖祖辈辈都想打通这座山,哪那么容易?”
但机器日夜不停地响着。有一天放学,我绕到施工处,看见父亲也在那里。他不再是石匠,成了施工队的一员,脸上沾着泥浆,却闪着我从没见过的光。晚上回家,他破天荒地跟我讲起隧道那头的世界:“听说那边有铁路,能通到省城,再通到海边。”
两年后隧道通了。第一辆车穿过时,全村人都站在洞口。当光亮从另一端透进来,我听见身边的老人们哭了。那一刻我明白,曾经的不可能,需要的只是时间和坚持。
十七岁,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。那是第一次走出大山。坐在破旧的中巴车上,隧道很短,只有三分钟,可我觉得像是穿越了几个世纪。山那边果然是另一个世界——平坦的田野,宽阔的公路,还有冒着烟的工厂。
在县城,我第一次摸到电脑。那个方方正正的盒子,按几个键就能知道天下事。我颤抖着手输入“山外面是什么”——屏幕上瞬间出现了大海、沙漠、草原,还有我从没想象过的高楼大厦。那一刻,我的心跳得厉害,原来世界这么大,而了解它,只需要轻轻一点。
大学我选了计算机专业。坐在明亮的机房里,我常常想起老家那台吱呀作响的旧电视,只能收到两个台,雪花比图像还多。而现在,通过这根细细的网线,我能听到哈佛教授的课,能看见巴黎街头的实景,能和地球另一端的人聊天。
去年回家,我给父亲买了智能手机。他一开始是拒绝的:“我这双凿石头的手,哪会用这玩意儿?”但当我教他通过视频,看见在广东打工的姐姐,看见她刚出生的孩子时,父亲的手在抖。他戴着老花镜,脸几乎贴在屏幕上,嘴里喃喃:“这怎么可能呢?这么远,就像在眼前一样。”
那一刻,我看见这个凿了一辈子石头的硬汉,眼角有泪光闪烁。
最让我感慨的是今年春节。我们全家围坐,用手机和远在加拿大的表哥视频。他在那边展示着漫天的雪花,我们在这边让他看满桌的年菜。奶奶对着手机喊:“娃啊,饺子还是热的呢!”屏幕那头的表哥笑了:“奶奶,我都能闻到香味了!”
挂了视频,奶奶坐在窗前发呆。我走过去,她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爷爷走的时候,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在外的表哥,说这一别,可能就是一辈子见不着了。要是他知道,现在天天都能看见,该多好。”
我望向窗外,曾经觉得永远翻不过的大山,如今隧道里的车灯像流动的星河;曾经以为走不出去的村子,现在通上了宽带;曾经觉得永远见不到的人,如今随时都能面对面说话。
这些变化不是一夜发生的。是无数双手,无数个日夜,一点点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就像那条大河,虽然还在向东流,但我们学会了造船、建桥,甚至让它发电,照亮千家万户。
夜深了,我打开电脑,开始写代码。屏幕的光映在脸上,我想起那个爬在槐树上的孩子。如果能够穿越时空,我想告诉他:孩子,保持你的好奇,保持你的不相信。这世上没有永远的“不可能”,只有等待被实现的“可能”。
山还是那些山,但它们不再是阻隔。河还是那条河,但它带走了时间,带来了改变。而我相信,今天我们认为的很多“不可能”,正在某个地方悄悄发芽,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天。
就像奶奶现在常说的:“这日子啊,过得比河水还快,变得比云彩还让人想不到。”她说这话时,不再望着远方,而是笑眯眯地看着家里每个人,看着这个曾经她觉得不可能拥有的热闹晚年。
是啊,曾经的不可能,现在都成了真。而今天的每一个“不可能”,或许正是明天的寻常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八亿典藏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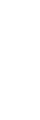 八亿典藏文章
八亿典藏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34)
1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22)
2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115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2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0)
5因为小事吵架冷战,他先发来 “想你了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