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上初中那会儿,家离学校远,得穿过大半个县城。一开始,我是极不愿意坐那辆车的。十四五岁的年纪,正是虚荣心像野草一样疯长的时候。看着同学们要么骑着漂亮轻便的新车,要么被父母用摩托车、甚至小轿车接走,我心里头总不是滋味。我爸那辆破旧的“永久”,还有他跨上车时那略显笨拙的背影,成了我羞于示人的一部分。
我总记得一个秋天的傍晚,天阴沉沉的,下着细密的冷雨。放学铃声一响,同学们像出笼的鸟儿,呼啦啦涌向校门。我磨磨蹭蹭地收拾好书包,心里祈祷着雨快点停,或者我爸今天有事来不了。可走到校门口,一眼就看见了那辆熟悉的车,和他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,外面套了件透明的薄雨衣,没打伞。雨水顺着他花白的鬓角流下来,他正踮着脚,伸长脖子,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焦急地寻找着我的身影。
看到我,他眼睛一亮,赶紧招手。我低着头,几乎是跑过去的,恨不得立刻消失在同学们的视线里。
“快,上车,雨大了。”他利索地脱下自己的雨衣,不由分说地罩在我身上,把我裹得严严实实。他自己则只戴了顶旧草帽。
我扭捏着不肯上后座,小声嘟囔:“爸,我自己跑回去吧,没多远。”
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,眼神黯淡了一下,但什么也没说,只是用那双布满老茧、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,用力拍了拍后座那块他亲手钉上去的木板,“上来,路滑,别摔着。”
那语气是不容置疑的。我只好侧身坐上去,把脸埋在他湿漉漉的后背上,尽量不让别人看见。车子“嘎吱”一声,沉重地启动了。雨点打在他的草帽上,发出“噼里啪啦”的声响,打在他的脸上、脖子上,他时不时要腾出一只手来抹一把脸。我躲在他的雨衣里,闻着他身上混合着汗水和机油的味道,听着他因为用力而略显粗重的呼吸,还有那破车链条永不停歇的“嘎吱”声,心里头五味杂陈。有羞愧,有心疼,还有一种说不清的烦躁。
风裹着雨丝,斜斜地刮过来。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背,想替我多挡一点风雨。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,他宽厚的背,像一堵墙。我偷偷把雨衣掀开一个角,撑在他头顶。他感觉到了,回头冲我憨厚地一笑:“没事,爸结实着呢,淋点雨不怕。”
就是从那个雨天开始,我好像才真正开始“看见”这辆车,和车上的父亲。
我开始注意到更多细节。比如,那辆车的车把,因为常年被他握着,磨得锃亮。脚蹬子有一边是坏的,他用铁丝牢牢地固定住。车铃早就哑了,但他每次拐弯或遇到行人时,还是会习惯性地用手去按一下,发出“咔哒”一声空响,算是提醒。车的横梁上,绑着一个他自制的工具盒,里面装着扳手、钳子和一小罐机油。车子半路出点小毛病是常有事,他总能就地停下,三下五除二地修好。
我也开始注意到他骑车的姿态。上坡时,他会整个身子离开车座,俯下身,用尽全身的力气一下一下地蹬,小腿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。我能清晰地看到他后颈上沁出的汗珠,和工装背上那片越来越深的汗渍。下坡时,他会轻松地直起身,让车顺着惯性滑行,有时还会哼几句不成调的老歌。那时,风会吹起他早已稀疏的头发,我能看到他眼角深刻的皱纹,像车辙一样。
这辆车,不仅载着我,还载过米、载过面、载过冬天取暖的煤块。它承载着我们一家平凡而具体的生活。车架上,布满了岁月的划痕和锈迹,每一道,似乎都有一个故事。
高二那年冬天,我发了高烧,请假在家休息。傍晚,烧退了些,我忽然想起第二天要交的作业本还落在教室。我急得不行,跟我妈念叨。我爸在一旁听了,放下饭碗,只说了一句:“我去拿。”
那天雪下得很大,是那种鹅毛大雪,地上很快就白了。我妈劝他,明天跟老师解释一下算了。他摇摇头:“娃的学习要紧。”说着,就推着那辆“永久”出了门。
一个多小时后,他回来了。像个雪人。头上、肩上、眉毛上,全是厚厚的积雪。他从怀里掏出我的作业本,干爽温热,没有沾上一片雪花。而他自己,嘴唇都冻紫了,不停地跺着脚,哈着气暖手。那辆自行车呢,更是被冰雪糊了厚厚一层,推起来比往常更显沉重。
我接过那本带着他体温的作业,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只是默默地拿起扫床的笤帚,帮他拍打身上的雪。他看着我,满足地笑了,那笑容,融化了他脸上的冰霜。
后来,我考上大学,去了很远的地方。离家那天,是他用那辆车,驮着我的行李,送我到长途汽车站。一路上,我们都没怎么说话。临上车时,他塞给我一沓皱巴巴的钱,低声说:“在外面,别亏待自己。爸……爸没本事,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”
我坐在车上,看着窗外。他没有立刻离开,而是推着那辆旧车,一直站在路边,望着我。他的身影在车窗外越来越小,那辆斑驳的“永久”也越来越小,最后,缩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,凝固在我青春的尽头,也凝固了我所有的泪水。
如今,我也有了自己的车,可以轻松地遮风挡雨。可我却常常想起那辆“嘎吱”作响的永久牌二八大杠,想起父亲奋力蹬车时弓起的背影。那辆车,很旧,很慢,它走不过柏油路上飞驰的汽车,也走不过日新月异的时代。但它却稳稳地,走过了我所有的年少时光,走出了我人生最初、也是最坚实的那条路。
它载着的,不是一个少年脆弱的虚荣心,而是父亲沉甸甸的、从不言说的整个世界。那“嘎吱——嘎吱——”的声音,不是疲惫的叹息,是岁月的歌,是一首用沉默和汗水写成的,关于爱的诗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八亿典藏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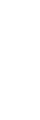 八亿典藏文章
八亿典藏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34)
1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22)
2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115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2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0)
5因为小事吵架冷战,他先发来 “想你了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