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轻轻敲了门。林教授坐在堆满书籍的办公桌后,只抬眼看了我一下,示意我坐下。他翻看着我的论文,办公室里只有纸张摩擦的“沙沙”声,每一声都像敲在我的心坎上。大约二十分钟后,他合上了稿子,摘下老花镜。
“小张啊,”他习惯性地用指节敲着桌面,“你的田野调查做得确实很扎实,资料也很丰富。但是,你的问题就在于,太‘扎实’了。”
我愣住了,一时没明白“太扎实”怎么会是问题。
“你这篇文章,像一本详尽的调查报告,罗列了太多现象,但缺乏一个核心的理论框架去统领它们。”他顿了顿,看着我迷茫的脸,尽量把语气放得缓和些,“你看,你提到了草编技艺在不同地区的差异,也记录了老艺人的口述史,但你并没有回答一个‘为什么’。为什么这种技艺在A村以这种形态存在,在B村却是另一种?背后的社会结构、经济因素、文化心理是什么?你没有深入挖掘。简单说,你这篇文章,有‘肉’,但没有‘骨头’。”
他的话像一盆冰水,从头顶浇下来,让我浑身冰凉。我试图辩解:“林教授,我只是想原原本本地把这种技艺和艺人的状态记录下来,我觉得它们本身就有价值……”
“记录是基础,但学术研究需要超越记录。”他的语气不容置疑,“按照现在这个思路,深度不够,创新性不足,肯定是不行的。你需要大改,甚至……我建议你换个题目。”
“换个题目?”我感觉自己的声音都在发抖。一年的心血,无数个日夜的奔波与伏案,被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否定了。那一刻,委屈、不甘、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,几乎将我淹没。我拿着那本被宣判了“死刑”的稿子,失魂落魄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。
那个寒假,我过得浑浑噩噩。论文稿就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,但我连翻开的勇气都没有。我看着电脑里那些整理好的访谈录音、拍摄的精美的草编作品照片,还有那些老艺人拉着我的手,诉说着传承困境时浑浊而真诚的眼睛,心里就堵得难受。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,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学术。
转机发生在春节。我回到老家,心情低落地帮着母亲大扫除。在清理阁楼时,我无意中翻出了一个旧藤箱,里面是祖母的遗物。有几件她亲手编织的杯垫和小篮子,虽然旧了,但纹路依然清晰紧密。母亲看见,感慨地说:“你奶奶当年,可是村里编东西的一把好手,花样都是她自己琢磨的,和别人家的都不一样。”
就是这句话,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脑中的迷雾。对啊!“不一样”!林教授说我缺乏“为什么”,而奶奶的“不一样”,不正是最鲜活、最个体的“为什么”吗?我之前的调查,过于追求宏观的、整体的“流变”,却忽略了每一个具体的手艺人,他们所处的独特环境、他们个人的生命经历、他们的喜怒哀乐,是如何像刻刀一样,塑造了他们手中那独一无二的技艺形态的。我的论文,缺的不是理论的“骨头”,而是那根能将所有材料串起来的、带着体温的“魂”。
那个春节,我几乎没有出门。我重新扑到那堆“被判死刑”的资料上,但这一次,我的视角完全变了。我不再试图构建一个宏大的叙事,而是像侦探一样,去追寻每一个访谈对象背后的故事。为什么李大爷的编法特别粗犷?因为他年轻时是伐木工,手劲大,审美也偏向雄浑。为什么王阿姨总喜欢在作品中编入一种特殊的花纹?那是她记忆中早已消失的故乡的图腾。我把每一个手艺人,都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,把他们的技艺,看作是他们的生命史与地域文化互动的结果。
我几乎重写了整篇论文。我没有引入多么高深莫测的理论,而是用一种近乎白描的、充满细节的笔触,去讲述这些手艺人和他们手艺的故事,并在故事的自然流淌中,让那种个体与时代、技艺与生命的张力自己浮现出来。我写得非常投入,常常写到深夜,感觉自己不是在敲键盘,而是在和那些远方的艺人对话。
再次把论文交给林教授时,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。我依旧紧张,但心里多了一份踏实。林教授看完,沉默了良久。最后,他叹了口气,说了一句我至今难忘的话:“我依然认为你之前的理论深度不够,但是……你这篇文章,有一种打动人的力量。它很‘真’。既然这是你坚持的方向,那就这样吧,我允许你提交。”
他的话,算不上赞扬,更像是一种无奈的放行。但我已经心满意足。至少,我守住了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。
之后的日子,我毕业,工作,那篇论文和其他无数毕业设计一样,被束之高阁,我以为它的生命就此结束了。直到一年后,我接到母校打来的电话,通知我,我那篇关于草编工艺的论文,意外地获得了那个年度全国性的“民间文化研究新锐奖”。
在颁奖典礼上,评委的评语是:“该作品摒弃了僵化的学术套话,以深具人文关怀的视角和细腻生动的笔触,深入民间肌理,捕捉到了传统工艺在时代变迁中跳动不息的脉搏。其价值不仅在于学术上的发现,更在于其对文化遗产所倾注的情感与温度,展现了年轻学人难得的田野精神与叙事能力。”
那一刻,我坐在台下,百感交集。我想起了那个寒冷的冬天,想起林教授的否定,想起那个在阁楼上找到灵感的春节,想起那些倾注了我无数心血的字句。我没有怨恨林教授,反而有些感激他。正是他那次坚决的否定,像一块坚硬的磨刀石,逼着我褪去了所有浮华和依赖,回归到研究的本源——你所研究的对象本身。它逼着我找到了只属于我自己的声音。
现在回想起来,那段经历给我的,远不止一个奖项。它让我明白,有时候,最严厉的否定,或许正是命运用一种曲折的方式,指引你去往你该去的地方。它敲碎了那个渴望得到权威认可、遵循既定路径的我,然后,一个更真实、更坚定、更相信自身感受和判断的我,才得以从碎片中站起来。那条少有人走的路,开头总是布满荆棘,但只要你听从内心的声音,坚持走下去,或许,路的尽头,会有一份意想不到的星光,为你而亮。而那束光,也必将照亮你此后所有的跋涉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八亿典藏文章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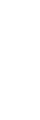 八亿典藏文章
八亿典藏文章
热门排行
阅读 (134)
1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22)
2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阅读 (115)
3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13)
4恋爱时的细心照顾,婚后的粗心忽略阅读 (110)
5因为小事吵架冷战,他先发来 “想你了”